彭兰教授新书《智能与涌现:智能传播时代的新媒介、新关系、新生存》的核心观点是:智能传播是人工智能技术与传播这两大系统的融合,也是人与机器两大系统的融合,但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会形成很多原有系统不存在的“涌现性”,呈现出全新而繁杂的传播图景、传播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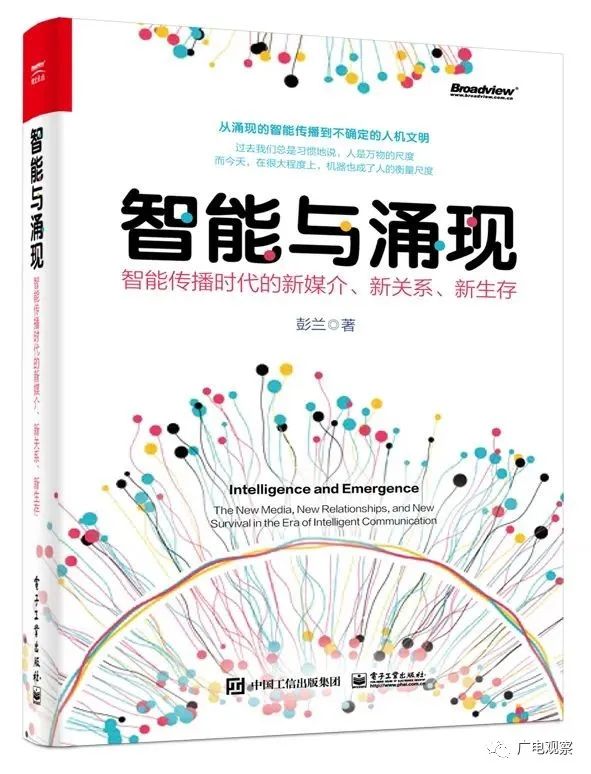
精彩书摘:
数据化如何影响人的生存
人的全息数据化必将全面影响人的生存。它带来了人的身体存在的新方式,拓展了人(包括其身体)与他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模式,发展出个人历史的新记录模式,并且进一步改变人与自我的关系,以数据化形式体现的外部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强大。
1. 量化自我实践的增强
由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 和技术专栏作家加里·沃尔夫(Gary Wolf)提出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这一概念,是指利用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技术等收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同方面的个人数据,用于探索自我、反思自我,从而获取自我认知的运动。
量化自我并非一个全新的现象,在可穿戴设备兴起之前,一些人也会对自己的身体数据进行观察与管理,如摄入的热量、体重等。人们对自己身体数据(如体温、血压、血糖等)的监测,是一种自我的量化管理。但无疑,可穿戴设备增加了人的自我量化维度,并使这种量化持续,成为一种长期的自我跟踪(self-tracking),特别是那些与身体运动、状态相关的量化。
健身人群是目前进行自我量化的主要人群之一,这既与健身本身所需要的精准的身体控制有关,也与这些人的健身目的有关。除提高身体机能外,健身也是一种提升自我形象的方式,这不仅仅体现为外在的身体形象,还体现为具有自控力的社会形象。这种形象要被看到,就需要分享,社交平台则是主要的分享渠道。如果总是分享身体本身的照片或视频,可能会给他人留下“自恋”的印象。而数据化方式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问题,跑步轨迹、跑步距离、配速等的展示,更为含蓄,并且对于营造良好形象来说,也有足够的说服力。
有研究者指出,青年跑步者是量化自我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热衷于通过身体数据展示自己的身体资本,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赋权感。跑步者通过数据进行团体交流,并获得了建构社会资本的一种新途径。类似地,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可穿戴设备实现了自我赋权,提高了人们的自我管理能力。但也要看到,这种自我管理并非是完全自主的,相关的数据一旦公开,就会受到他人反馈的影响。社交平台的互动,总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自我管理的过程,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即使不公开数据,个体对这些数据的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自我调节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社会规范的影响。
自我的量化总是依赖相关的设备和应用的,量化的维度受限于这些软硬件,软硬件本身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数据的精确性或可靠性。软硬件的开发者,特别是软件的开发者,他们所关注的量化维度,也总是带有商业化的考量,如哪些数据可能成为资源,甚至带来盈利模式。看上去自主的自我量化背后,仍有技术及平台的约束。使用者贡献的数据成为商业化的资源,甚至可能成为被平台出卖的商品。因此,量化的自我就是市场化的自我。
在量化自我的过程中,人们会受到各种指标的牵引,但很多指标并非是权威机构提供的,而是在社交平台的互动中产生的。一些意见领袖对这些指标的影响尤其明显。
例如,在体重、身材这样的数据上,虽然健康机构给出了健康的体重指数范围,但实际上人们(特别是年轻女性)所追求的目标,往往偏离了这些健康指标,有时甚至追求如“A4 腰”等社交平台的自造标准。
应用平台在应用中内嵌的指标标准对人们有很大影响,但这些指标的科学性未必经过严格检验。即使用户和平台参考的是科学指标,但对这些科学指标的理解与执行可能有偏差或误区。无论是社交平台自发形成的规则,还是其他机构制定的各种指标与规则,量化自我都会让人们对各种指标变得更为敏感,并且会努力遵循这些指标的引导,甚至在某些时候会走向机械化、非科学化、极端化。
在量化自我的实践中,人们究竟是因为身体的数据化而带来身体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可数字化)来理解这种“价值上”的“提升”呢?答案是两者并不必然互斥,甚至很多人同时获得了这两者。但是这种实践的确也可能走入一种误区,即对数据的追求,超过了对健康本质或生活本质的关注。
很多时候量化的自我不仅是给自己看的,还需要展示给他人看。量化自我的实践会与人际互动,甚至群体互动产生交融,也会受到来自他人的审视、评价。人们可能因此加大对自己的调节。因此量化自我的实践,并不一定意味对自我的自主控制力的增强,还对量化自我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思考,使我们可以更深层地理解个体赋权与外界约束两者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其他方向下人的数据化过程中也时时存在。
2. 个人历史与记忆建构的数据化、媒介化
在人被全息数据化的同时,个人历史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数据化记录,并通过媒介公开。个体的生活印迹、工作学习轨迹、社会活动行踪投射在数字空间中个体的各类账号的时间轴上,并散落在各种类型的虚拟空间、平台与终端上。构成个人历史的数据,既有人们自己的记录与“表演”,也有所在“单位”(或其他组织)及他人的记录,还有来自媒体的报道。其中有主动的公开,也有被动的披露,夹杂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双重色彩。一旦进入公共媒介,这些内容就不再是个体能完全控制得了的。
构成个人历史的数据在常态下是片段或离散的,但只要对它们进行有意挖掘、整合,就能拼贴出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线或相对完整的图景,甚至可能发现一些个人秘密。但更多时候,他人或外界对个体历史的认知,主要是基于从“当下”信息中提取的、被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对个体的记录与反映又是片面,甚至是扭曲的,有些信息可能被人有意曲解。个人历史被数据化、媒介化后出现的以上结果,意味着个体对自己在数字空间历史信息的不可控性。
个人历史的数据化,在某些方面意味着记忆的数据化,即记忆的外化与媒介化。这种记忆不仅与个人的记录方式有关,也与社会互动、存储平台等有关。个人记忆不再仅仅依靠个体自身,还依靠很多外部因素。
数据化的轨迹并不能完整反映个体的全部历程,但作为一种记录、记忆方式,有时数据比人的大脑记忆更为持久。当大脑记忆变得模糊时,人们需要依赖数据化记忆进行回顾。对这些数据的记忆是靠大脑之外的各种“外存”,如个人的终端、平台的服务器等记录。一旦数据记录的载体出现问题,则会导致记录与记忆出现破损。例如,某个手机的丢失、某个存放信息的服务器的损坏。过于依赖外存,会导致个人历史记录和自我记忆的残缺与失真。
当数据化的记忆成为常态时,人们的“黑历史”会以超出预期的时间与空间进行留存。由“黑历史”引发的个人危机事件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社会的层面看,个人历史的数据化意味着个体生命进入了生命政治的治理装置之中,个体数据成为治理层面维系社会安全和运作的基本方式。同时让每一个参与共同体和国家活动的个体,都必须按照这种可治理的方式来重新生产自身。但在这样的治理装置中的数据化个体,其鲜活的个体面孔、现实的个人境遇可能被移除或简化,最终成为一个个被统计的数据,或被计算的对象。
3. 数据塑造的数字自我与数字人格
数据不仅在记录个体的生命历程,还在建构一种数字化的自我。
学者蓝江指出,我们在网络中形成的数字痕迹,可以让智能算法精准地描绘出另一个自我,一个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自我。但是与之前的自我不同的是,这个自我并不在我们的内部,而是在那个无形的互联网中。它不是由我们的理性的自我意识构成的,而是由无数我们有意或无意的行为留下的数据构成的。
我们还可以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理解数字自我,它不仅是被数据描绘与算法分析出的自我,还是人们通过各种数据化行为主动表达的自我,并且在数字互动中被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所塑造的自我。这种自我会受到技术、媒介等的作用。数字自我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它体现在自我呈现、自我建构、自我认同等不同层面,并对现实自我产生影响。
从自我呈现层面看,数字自我既有现实自我的投射,也有基于虚拟空间特性对自我的修饰甚至再造。因为数字空间角色扮演的自由,表演手段与策略的多样化,使它更容易呈现自我的多面性。自我呈现的策略(真实还是虚构、积极还是消极)、自我呈现获得的反馈,也与自我认同有着关联。
从自我建构层面看,数字自我受到的关键影响来自数字环境中的认知参照体系。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在认识自我时,会将自我放在何种参照体系中进行认知的一种倾向。
按照以往学者的看法,每个个体的自我建构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从自身独特性定义自我、从自己与亲密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从自己和所从属团体的关系中定义自我,分别称为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和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也称为自我的三重建构。
数据化的表演,首先体现的是个体自我,但由于数字空间中社会互动范围的拓展及频率、程度的加深,参照体系变得多元。因此,个体自我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影响,他们会基于数据化表演结果的反馈进行自我建构的调适。三重自我之间的相互观照、博弈也变得频繁。
自我认同指的是在个体的生活实践过程中, 通过与他人及社会进行互动, 以及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 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况。自我认同包括自我的同一性的建构、自我归属感的获得、自我意义感的追寻等。
如前所述,当下的互动很多时候是在数字空间中以数据化方式进行的,自我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字空间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就有研究者担心,网络会带来自我认同危机。例如,自我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分离、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分离、自我与人的本质的分离,或者“信息在场”与“人身在场”、“网我”与“真我”、“自由个性”与“失个性化”的内在紧张。但除了危机,数字空间是否会给自我认同带来其他可能,还有待未来实践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与此同时,自我意识面临着数据化的可能。如研究者指出,既然自我意识——自我的核心内容的本质是一种被记忆的信息或信息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而信息是可以复制、移植和数字化的(如对过去经历的记忆),那么自我意识在信息的数字化越来越普遍的今天,也必然面临着被数字化的问题。数字化的自我意识在网络空间中被自我转换、自我掌控、被他者感知, 形成了网络空间中可控的自我, 呈现为鲜活的数字自我。
数据化生存会带来数字化的“人格”。对此,不同研究者的表述不同,如网络人格、虚拟人格、数字人格等,定义也有所差异。有法学研究者认为,数字人格是主体在网络世界所具有的身份和资格,是主体的信息化表现,是个人信息权利的有机结合和主体体现。也有研究者将其界定为以数字符号为载体的、代表虚拟空间的虚拟实践主体人格信息的集合。它来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的人格,是人在虚拟空间的人格代表。
在另一些研究者看来,数字化人格则是通过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勾画一个在网络空间的个人形象,即凭借数字化信息建立起来的人格或基于算法对数据本体的个人先前行为轨迹进行数字化描摹,并进行信用评级由此生成的数字化个人镜像,数字人格意在勾勒出数据本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可信任程度。
这些定义有些侧重于对数字化空间个体权利的关注,有些侧重于数字化的个人形象,还有些侧重于借助数据衡量的个人信用。对数字人格的不同界定,体现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不同关注重点。可以看到,近年对数字人格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数据与数字人格的关系,包括算法的影响。
在数字社会当中, 一个人的人格之塑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信息。个人以何种形象出现,依赖于个体的自我决定权, 包括个人对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权。数字人格具有双重面向: 对外的人格呈现和对内的人格隐匿。两者都涉及自我决定权, 前者涉及人格的信息是否公开,以及如何公开, 后者与前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涉及个体可以在无形的网络当中适度地隐藏自身以公开、自由的表达。
数字自我,也有可能遭遇“社会性死亡”。在不同语境下,“社会性死亡”的含义不尽相同,从出丑、尴尬到被围攻、失去网络名声,甚至无法在数字空间立足。对于后面的情形来说,社会性死亡是数字人格被否定、摧毁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一些权利的丧失。虽然有些权利并非是法律制度所赋予的。
从法学的角度看,数字人格的提出是为了讨论数字自我应该拥有的权利。无论未来数字人格权利会涵盖哪些范围,个体对自我产生的数据拥有的权利一定是核心权利之一。2021 年11 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所指的个人信息正是这类数据。这一法律从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各个环节制定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未来基于数字人格前提的权利讨论乃至实践也一定会随着应用的发展而深化。
从虚拟的“数字化生存”到现实与虚拟之间深层互动的“数据化生存”,我们似乎获得了更多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自我记录的可能,获得了更多便利的服务。但另一方面,当人被映射、拆解成各种数据时,既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自身数据的控制力,也会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多重控制。
与人相关的数据维度的不断丰富,并不意味着数据对人的反映是完整的,也不意味着人的一切都可以由数据塑造,仍然有一些人的本质属性无法变成数据,或者不应该成为数据。
(作者简介:彭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